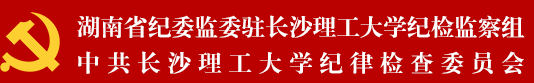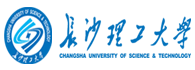與時間賽跑的人——鐘揚教授的兩個晝夜
一、凌晨的機場
凌晨4時。
天色微明,黑夜漸漸隱去,太陽還在積蓄力量。成都雙流國際機場候機大廳里,已經響起稀稀落落的腳步聲,伴著行李箱輪子劃過地面的聲音。
鐘揚掃了一眼筆記本電腦右下角的時間,合上電腦,連同一沓稿紙塞進身旁一個老舊的雙肩包,起立,掄包背上,一系列動作熟練流暢。站起身后,才發覺右腿關節疼得厲害,腳趾也痛。原地活動兩下,他便一瘸一拐地大步往機場柜臺走去。進出西藏的機票有時非常緊張,為了買到最早航班的機動票,他要早點去柜臺等著。這天運氣不錯,買到了6點多起飛的航班。
這些年,鐘揚的生活由“上海”和“西藏“兩部分組成:他是復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學科研和管理崗位“雙肩挑”;他同時還是西藏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第六、七和八批中組部援藏干部,西藏大學生態學一流學科帶頭人。在哪里他都是出了名的工作“瘋子”。
2017年5月3日,一天前剛過完53歲生日的鐘揚,在復旦大學忙完一天的工作,便馬不停蹄地到上海浦東機場趕最晚一班飛機前往成都,落地已是次日凌晨一點多。成都到拉薩的最早航班早上5點左右開始辦理登機手續,中間也就3個多小時,他習慣就在機場候著。一來需要處理一天的郵件,二來繼續完成手頭的一大堆工作。困了,就在機場的候機樓里找個座位打個盹。
他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次睡在機場候機樓椅子上了。看著午夜稍顯冷清的候機樓,他想起上海家中熟睡的妻子和大兒子,還有在山東濰坊住校的小兒子,心中涌出一絲歉疚。這一晚曉艷又沒睡踏實吧,她說我一出差她就夜里常常會醒。兩個孩子應該睡得正香,都是馬上要滿15歲的小伙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
5時20分。隨著排隊辦理登機手續的人群,他又往前挪了幾步,右腿還是疼得厲害。大概是在候機樓里著涼了,痛風的老毛病犯了,坐久了痛,站久了也痛。“痛風,痛風,痛起來要人發瘋”,每次發作起來他都喜歡這么自嘲。
他下意識地摸了下衣袋,衣袋里有幾張小卡片,密密麻麻記著各種待辦事項,他從里面抽出一張。這是他多年的習慣,每做完一件事就劃去一條,事情做完紙片就扔了,做不完的謄到下一張卡片上。他迅速把當天要做的幾件事在腦子里捋了一遍,又在卡片上加上幾條。
時間真不夠用。這些年,他一直有一種緊迫感:高原反應的危害可能要5到10年后才顯現,希望老天再給我10年時間。兩年前的那場大病后,他的緊迫感更強了。家人對他生病后“變本加厲”的工作節奏很擔心,80多歲的老父母打電話,希望他能減少一點工作,他每次都說,我沒事,好著呢。每次電話說不了幾句就要掛,要么是馬上要上課了,要么是馬上要開會了,要么是馬上要登機了,急得老母親只好寫信勸他。去年母親的一封長信還躺在他辦公桌的抽屜里。
妻子看他回到家后疲憊的樣子心疼,可幾次勸說無效也就不再言語了。“他這人挺難改變的,我們能做的就是不給他加重負擔。”妻子懂他,默默地數著他一次次往返的日子。他對妻子說,希望老天再給我10年,把人才梯隊真正帶起來。等到西藏的事業能夠可持續發展,那時我會考慮留在內地幫助西藏。
登機手續辦妥,窗外天色亮了些,灰白色鑲著淡淡的紅邊。鐘揚在登機口附近的長椅上坐下,打開筆記本電腦,繼續剛才沒有處理完的事情。他非常善于利用碎片時間,能夠做到隨時打開電腦就工作,被打斷后毫無過渡就能立刻接上。他頗以這一“特殊能力”為傲。這讓他從各種縫隙里擠出了盡可能多的工作時間。
因為這種“見縫插針”工作法,他的雙肩包里除了筆記本電腦,還有寫滿密密麻麻字跡的各種手稿。他會在等人的時候寫文章,也會在飛機上寫文章,還在會議主席臺上偷偷寫過文章。一次,有個學生想幫老師接一下雙肩包,一不留神差點兒沒接住。他的學生趙佳媛說,大家掂量過老師的雙肩包,得有幾十斤吧,要兩個人才能比較輕松地拎起,他卻走到哪里都背著,上課、出差、去野外。
雙肩包的背帶早就磨毛了,表面的織布好幾處都磨破了,那里面裝著山山水水的跋涉,是他行走在祖國大地的最好見證。
二、另一個家園
上午6時許。
天剛剛亮,從成都飛往拉薩的航班起飛。“順利的話8點前到拉薩,正好投入一天的工作,自己趕一趕,復旦和西藏大學兩邊的事情就都不耽誤。”鐘揚曾得意地向學生拉瓊炫耀自己摸索出來的這套“最佳時刻表”。
這確實是一份緊湊得不能再緊湊的時刻表。擠壓時間的同時,一再擠壓的,還有他的身體。進藏會有高原反應,離藏則會醉氧,即使西藏當地人往返西藏也會選擇先適應一兩天,但他從來都是不休息就直接開始工作。朋友們見到他都說,你不要命啦,這么拼!可他就是慢不下來,放不下來,他心里急呀,時間不等人。在他這里,往返上海和西藏,4000米的海拔落差頻繁切換,就像是上下樓一樣稀松平常。他的名言是,不能因為高原反應我們就怕了嘛,科學研究本身就是對人類的挑戰。
起飛最初階段,他通常會抓緊時間瞇一會兒,基本一合眼就睡著了。飛機進入平飛階段后,燈一亮他就醒了,15分鐘的睡眠讓他覺得舒服多了。從雙肩包里拿出學生論文的打印稿繼續修改,又批注了幾十頁。
“打開遮光板,調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隨著飛機下降,他向舷窗外望去。5500萬年前青藏高原由于板塊碰撞而隆起,山峰起伏跌宕的峻利棱角,山頂的皚皚積雪清晰可見,高山間散落著星星點點的草甸和海子,像鑲嵌著多彩的寶石。他已無數次從空中俯瞰這大開大合縱橫捭闔的切割,每一次,哪怕只一眼,也讓他生出無限壯志和溫情。
西藏是他的另一個家園,是他精神的豐饒園地。他的野外工作以達爾文為榜樣,這些年他對青藏高原植物的研究再次印證了達爾文的理論。在青藏高原類型多樣的極端環境下,植物與環境之間長期相互作用,經過強烈的自然選擇,產生了許多適應極端環境的基因類型。把這些特殊的基因資源收集、研究清楚了,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發展乃至人類命運都具有非凡的意義。
鐘揚對植物學的興趣緣起于大學畢業后的工作分配。1979年,整個社會呼喚“科學的春天”,年僅15歲的鐘揚高一就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無線電專業。1984年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研究所。最初,他和同一批分配來的大學生、后來成為他妻子的張曉艷合作進行荷花分類研究。因為每天清晨去武漢植物園采集荷花數據,植物學的“門外漢”一下子沉浸其間。他花了整整兩年業余時間,旁聽了武漢大學生物系所有課程。為了更多地了解每種植物的特性,一有空就“泡”在武漢植物園里,熟稔上千種植物。無線電專業背景讓他敏銳地捕捉到計算生物學研究方向,很快就取得學術上的進展,成為所里最年輕的助理研究員。20多歲的他已成為當時國內植物學領域的青年領軍人物。
鐘揚33歲就當上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副所長、副局級干部,2000年卻放棄職級待遇到復旦大學當一名普通教授。這讓很多人大跌眼鏡。
對于這一選擇,鐘揚從不后悔。他每做一件事情,都在追隨他的夢想——
在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研究所工作的16年,他是走在時代前列的科研工作者,是熱情的傳播者——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國門初開,他不斷地把國際上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紹到中國,推動我國植物學研究的發展。
從副局級所長到高校的普通教授,也是一次追夢——隨著科教興國戰略實施,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啟動,他希望從科學家轉型為既搞科研又搞教學的大學教授,既是圓自己的教師夢,更是追隨時代的號角。他迫切需要把掌握的知識,更快速地傳遞下去。
到復旦一年后,他的《簡明生物信息學》出版了。這一學科當時在國際上也是剛剛起步,在全球也還沒有一本成體系的教材!多年后,生物信息學發展得如火如荼,證明了他的研究的前瞻性。迄今為止,這本教材依然是國內發行量最大、選用高校最多的生物信息學教材。
如果沿著這條實驗室研究的路走下去,以這位青年學者的聰慧和勤奮,可以想見他能夠抵達的學術高度。而這時,他將目光投向我國生物資源最為豐富而人才極度缺乏的青藏高原。從學術研究的最高端、最前沿,轉投“打地基”的工作——采集種子。他要先從打基礎做起。
鐘揚是一位極具戰略眼光的優秀科學家。他說,好的植物學研究一定不是在辦公室里做出來的。在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生物多樣性排名是很低的,但是卻聚集了我國近一半的生物學家。祖國那些生物資源豐富的地方才是生物學家應該去的地方。他選擇去西藏,因為那里是國家生態安全戰略之地。那一年,他37歲。
走進青藏高原,踐行學術援藏,是他的又一次逐夢——他要為幾十年、幾百年后的人類儲存下種子和希望。在這一過程中,他深刻地感到西部地區在科技和人才培養上,還存在巨大差距。他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要把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科學研究和少數民族的高等教育帶進新時代的建設進程中。
16年堅持學術援藏,連續成為中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在雪域高原跋涉40多萬公里,收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他帶領團隊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種子的空白。
設在云南昆明的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啟動于2004年,迄今已保存了我國野生植物種子9800多種,占我國種子植物總數的三分之一,躋身世界三大種質資源庫之列。其中,大量青藏高原的珍貴種子來自鐘揚和他的學生。
很多人不理解。在上海同樣可以做研究、帶學生,或許還能取得更大的科研成就,甚至獲得“院士”稱號,他卻去做這樣一項高勞動強度、低回報的“賠本”工作,走了一條緩慢而艱辛的道路。
對于這一選擇,他從不后悔。別人的再好,那是別人的。保存種質資源已經成為一項基礎性、戰略性的工作。我們自己的資源,如果不掌握在自己手上,是很危險的事情。西藏是一座寶庫,種子是留給未來的財富。
一次次在接近巔峰時轉身,另起爐灶,他的身上有著“功成不必在我”的豪邁與灑脫。他心里想的就是做事,做對人類有益的事。
一次次轉身,向著新的高地不斷推進,他的身上有著“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韌與頑強。別人孜孜以求的東西,到他這里可以變得很“輕”,對自己所肩負的理想與使命,他看得比什么都“重”。
這些年,他唯一后悔的是,來西藏太晚了。
飛機平穩地降落在拉薩貢嘎機場時,機艙電子屏上的時間剛剛跳過9點。鐘揚從經濟艙狹窄的座位上站起身,再次背起雙肩包,拖著疼痛的腿大步往外走。
微涼的山風撲面而來,捎帶著拉薩河的氣息,他大吸了一口。
拉薩的天空很藍,比藍更藍。
三、在西藏再干10年
拉瓊已經在貢嘎機場出口大廳等著老師了。
拉瓊是鐘揚在西藏大學帶出的第二個藏族植物學博士。2006年夏天,拉瓊剛從挪威卑爾根大學讀完植物學碩士學位回到西藏大學,那段時間鐘揚也正在西藏大學,和學生扎西次仁一起做西藏巨柏的研究。他們在藏東南地區沿雅魯藏布江兩岸調查巨柏的分布與生境,要將現存的西藏巨柏逐一采樣、登記造冊。
拉瓊第一次在西藏大學的辦公室見到鐘揚,他正和其他老師們一邊整理采集來的巨柏樣本,一邊講述最近一次野外考察的收獲和各種趣事。睿智、自信、淵博、幽默、熱情,初次見面,拉瓊就被眼前這位上海來的學者折服了,暗下決心要跟著他攻讀博士學位。
“你剛從國外回來,千萬別把英語給丟掉了。”有些內向的拉瓊話還沒出口,他就大聲說,“你的優勢很突出,盡快報考復旦的博士研究生。”他的爽直讓拉瓊馬上放松了。
拉瓊感動的是,見過這一面后,鐘老師就記住了他。有一次從拉薩趕回上海途中,還專門從機場打電話詢問他報考準備情況。學生的大事小事他都記在心上。他會記得每個人的老家是哪里,家中有幾個兄弟姐妹,連學生發表論文時英文名怎么寫他都會考慮。
2011年,拉瓊考取鐘揚的博士研究生。跟隨老師11年,在拉瓊心中,鐘老師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良師、益友,也是事業發展的精神支柱。如今拉瓊已成長為西藏大學理學院的教授、生態學博士生導師。
想到又能見到老師,一早,他就興奮地開著“牛頭車”出門了。在藏區大家都把豐田越野車稱為“牛頭車”,良好的通過性最適宜野外科學考察。
“鐘老師!”看到熟悉的身影一瘸一拐地闊步走來,拉瓊趕緊迎上去。
“沒事,一會就好,咱們走,抓緊時間。”注意到拉瓊的眼神有些遲疑,他說著就徑直往副駕駛座位走,一下子把拉瓊落在后面好幾米。
拉瓊快步跟上準備開車,只見老師在對面扶著車門,用力撐起自己的身體,緩慢地往里挪進一條腿。越野車的車架高,再拉一把,才挪進另一條腿,坐了下來。
花了有三分鐘吧。那三分鐘,拉瓊覺得有半個世紀那么長。剛注意到老師遲緩的動作時,拉瓊直后悔自己因為著急竟忘記先去幫老師。他想下車過去扶一把,老師的神情叫住了他。自從2015年那場大病之后,再次進藏,拉瓊明顯感覺到,老師的身體大不如前了。這種越野車他以前常坐,可現在,有時連上車和下車都很費勁。
“鐘老師,下次您能不這么趕時間嗎?”看著老師的疲態,拉瓊不忍。這么大的科學家,一點不把自己當專家,什么都不講究。
“沒事、沒事,我很好。玩的就是心跳嘛!”“我還要在西藏再干10年呢!”喘氣還沒定,他就用帶著兩湖人特有口音的普通話逗拉瓊。他黝黑憨厚的笑容有一種天然的感染力,詼諧的語調透著革命樂觀主義的豪情。可此刻拉瓊聽著,只覺得心里酸酸的。
從拉薩貢嘎機場到西藏大學新校區,一小時左右車程。一路上說起今年藏大生態學博士點招到了第一名藏族博士生,索南措。“太好了!太好了!”鐘揚連聲說道,開心得像個孩子。拉瓊也高興,老師這幾年一直在物色適合的藏族學生,鼓勵他們來報考。
在鐘揚眼里,藏族學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所達不到的。他們對這片土地有感情,對這里生長的植物有感情,采種子,他們知道哪里該采,哪里不該采,采多少才合適,很多時候不是用科學的標準能說清楚的。藏族學生無論在哪里學習、深造,大多數都將回到西藏,他們必將成為科學研究中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軍。所以,他特別重視培養藏族學生,從他們當中發掘高端學術人才。
80后藏族女生德吉就是在鐘揚的感召下決心報考博士的。碩士對一名藏族女孩來說,已經是很高的學歷了,十年前的西藏大學,博士也并不多。鐘揚發現德吉是一棵好苗子,盡管專業是化學,但可以從事生物化學交叉學科的研究,便問她想不想繼續考博士,初為人母的她當場就愣住了,在此之前,她從未動過這個念頭。2017年,德吉成為鐘揚帶出的第一位藏族女博士,也是最年輕的一位,是他培養的七個少數民族博士中新近畢業的一名。
青藏高原的特殊生物環境和生物資源為我國科學家開展原創性的工作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鐘揚說,我們需要建設一支年富力強、野外經驗豐富、多民族融合的科研團隊。他的夢想是,尋找高端人才培養的學術援藏新模式,讓西藏的生態學研究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拉瓊還記得,2009年,老師受聘成為西藏大學首位長江學者。在全校大會上,他放下豪言:“如果西藏大學拿不到博士學位點,我絕不離開西藏!”那時,西藏大學在理工醫學科連一個碩士點都沒有,植物學專業也沒有教授,甚至沒有一位老師有博士學位。
很少有人會這樣表態,當時在場的老師和學校領導都很激動。但過后又有些懷疑,擔心只是一時興起的大話。
事實證明,鐘揚是個言出必行的人。他想了很多辦法,切實提高西藏大學的科研能力和多學科之間的聯動,在西藏大學生物學碩士學位點和生態學博士學位點獲批后,為了優化招生,他還鼓勵自己在復旦大學的生源到藏大報考他的研究生。他多次邀請藏大教師去復旦大學交流學習,都是他出的經費。為了鼓勵藏大老師申報科研項目,他不但親自傳授申報經驗,凡是寫了項目申報書的,交給他審,他都會幫助修改,不管申報成功與否,他都自費給每位老師補助兩千元。
2011年,西藏大學生物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點獲批。2013年,西藏大學生態學博士點獲批,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沒有理學博士點的空白。2017年,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雙一流”建設名單。
四、學生永遠是饑餓的
“到家啦。”
鐘揚在藏大的宿舍是中坤專家樓中的一座,說起來是他個人的宿舍,其實很多人都有鑰匙。兩層小樓的每個房間里都放了很多藏式卡墊床——白天當藏式沙發坐,晚上可以當床睡。認識或是不認識的人,只要是來西藏考察、做科研工作的,鐘揚都會接待他們住在這里,給他們的高原工作提供便利。
在這之前,好幾年他都住在教工周轉房里,學校給他分配的這處專家宿舍,他一直不肯搬,總說已經夠住了,嫌搬家太耽誤時間。最后還是趁他不在拉薩的時候,幾個老師和學生幫他把東西搬進了專家宿舍。
搬進來之后他也覺得挺好,一來可以接待更多來西藏的人,二來有廚房,熱愛食物的他給學生們做飯更方便了。做試驗的地方也有了,他把樓前面的小院改造成了實驗田,種上擬南芥和抗寒水稻。這是西藏特有生態型的擬南芥,十多年來鐘揚一直帶著學生在尋找,最終,他的兩位學生許敏和趙寧,在堆龍德慶的羊達鄉,海拔4150米的山上找到了。經過分子生物學分析,證明它是全世界一個嶄新的生態型。鐘揚將其命名為“XZ生態型”,既是兩位年輕人姓的縮寫,更是西藏首字母的組合。
“鐘老師,中午就別在宿舍做飯了,我們在小飯店吃點,你抓緊時間休息會兒。”拉瓊心疼老師。
“不行不行,還是老樣子,去超市買點菜,我來做飯,一會你去把大家都叫來。”平常風風火火的鐘老師,這個時候卻不急了,固執地要洗菜做菜。
一群學生涌進屋子,小樓里一下子熱鬧起來。他放下雙肩包,拿出筆記本電腦,把論文修改稿放在桌上,就開始下廚。
拉瓊每每驚訝于老師做菜的速度,一會的工夫一桌菜就擺出來了。還特別好吃,雞蛋炒青椒、熏肉炒蕨菜都是拿手好菜,大家都特別愛吃。看大家吃得開心,他更開心。他專門總結過,自己的絕招是火開得夠旺。這天他還做了道回鍋肉。學生邊珍向老師“正經拜師”學藝,這是他傳授的第一道菜。邊珍曾有出國學習一年的想法,他便提醒她,學幾道菜非常有必要。
在學生中,有一句他的名言流傳了十幾年:“Students are always hungry(學生永遠是饑餓的)”。他有幾個習慣:在復旦大學時,早餐習慣性買兩份,自己吃一份,另一份放在實驗室,總有一個學生沒吃早飯,如果沒人吃他就中午自己吃;午飯,多數時候是盒飯或方便面,他會盡量跟不同的學生一起吃,這樣能跟學生有更多接觸。晚飯經常很晚,有時就成了宵夜,這時他會招呼實驗室的所有學生一起,大家邊吃邊聊。在西藏大學,討論到飯點了,他就親自掌勺給大家做一桌菜,一邊吃,一邊討論。
同事和學生眼里的鐘揚是一個有魔力的人,是出色的領導者,是優秀的教育者,有科學的思維方式、廣闊的視角和獨特的人格魅力,他的熱情和努力能點燃所有人,去盡情擁抱無限的可能性。
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包信和曾與鐘揚在復旦大學共過事。在他眼中,鐘揚是一個很有才華和能力的人,走到哪里都能夠很快脫穎而出,獨當一面。他更是一個純潔、高尚的人,坦蕩無私的品格深深感染了和他交往的每一個人。
五、深夜的一盞燈
山頂上,一輪皎潔的月亮升起。
鐘揚宿舍的燈還亮著,他還在忙碌。這次進藏,鐘揚的日程表像往常一樣排得滿滿當當。
下午3點半。鐘揚作為評議專家,參加了西藏大學醫學院博士生答辯會。他對西藏地區植物的研究,最早就是從藏藥開始的。從西藏大花紅景天、手掌參,到高原香柏、山嶺麻黃等等,這些年他始終關注這一領域。
他認為,種子可以為人類提供水果、花卉,改善人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糧食作物,還有醫藥。包括我們現在了解到的青蒿素,也是來自植物,如果有了它的種子,就可以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進行栽培,從中獲取青蒿素這樣有用的藥物。
下午5點。鐘揚開始與西藏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一起處理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方面的事情。他在西藏大學的宿舍就像是“診室”,大家都帶著問題找他請教,一刻也停不下來。
看著那個忙得都顧不上喝水的高大身影,徐寶慧覺得親切又踏實。徐寶慧原先在理學院任黨委書記,有幾年和鐘揚共用一間辦公室,之后調到文學院任黨委書記。在他印象里,鐘揚一年到頭就是幾件衣服,兩只手就能數得過來,幾乎就沒穿過什么新衣服。這次來,穿的還是那件格子襯衫和磨得發白的牛仔褲。
記得他唯一的一次穿新衣服是有一年藏大開學。一進辦公室,鐘揚就得意地問徐寶慧:這件衣服怎么樣?他高興地說,這是過年時他的小兒子花了120塊錢壓歲錢,在復旦旁邊的五角場給他買的。他為此開心又自豪。
他的生活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不舍得給自己多花一分錢,可對藏大師生,一出手就是“大手筆”。
剛來西藏大學時,得知很多藏大學生從沒走出過西藏,他出資發起“西藏大學學生走出雪域看內地”活動,組織80多名藏大學生赴上海學習,開闊眼界,整個活動花費幾十萬。誰都沒想到,前前后后都是他自掏腰包,他從不提起,直到好幾年后大家才發覺。
有學生做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資金不夠,他就出錢補上。西藏大學給了他一筆科研獎勵,他分文不動,主動提出給幾個經費不足的學院使用。
2012年,西藏大學生物學專業招收首批7名碩士研究生,但學校的公共基礎課還跟不上,他就聯系武漢大學,選派這批學生到武大學習一年。這些學生家境都很貧困,他放心不下,好幾次專門到武漢看望,一來就帶著他們去東湖邊最好的館子吃武昌魚,還當場給每位學生一千元現金作為生活補助。他還帶著學生到他在武漢的家,交代年邁的父母平時多照顧,給他們改善生活。幾乎每個雙休日,學生們都會去吃他父親的拿手好菜——紅燒肉。
只要鐘老師在,大家的心就特別定。鐘揚常說,到拉薩不是出差,是回到他在這邊的家。這些年,他待藏大同事如家人,大家也早已把他當作交心的兄弟。2015年5月2日,得知鐘揚突發腦溢血,徐寶慧趕到上海看望。他和大家一樣,心疼鐘揚的身體,也擔心他以后再也來不了西藏了。鐘揚不在,很多還沒做完的事大家不知從何入手。沒想到,幾個月后,他那招牌式的憨厚大笑又回響在西藏大學理學院的樓道,那一刻,整個理學院都沸騰了。
同事們提醒他注意身體,把節奏放慢些。最開始他還能管住自己,有兩次是坐著高鐵進藏的。很快,他就把醫生“不能再去西藏”的叮囑放在一邊,像鐘擺一樣忙碌了起來,又回到了每天只睡三小時的生活。
在學生面前,在工作面前,他似乎永遠精力無窮。他是把心都捧出來交給了西藏,交給了學生,交給了面向未來的事業。
夜已深了,徐寶慧走出樓外,抬頭看著鐘揚宿舍依然亮著的燈,心里說不出的溫暖。
晚上11點。
“坐診大夫”總算忙完了當天的工作,打開電腦在網上評閱國家基金委的申請書。
凌晨1點。
鐘揚開始處理郵件。很多人都發現,常常當天下午甚至晚上和他溝通的事情,他半夜就給對方發去郵件。這些郵件主題不一,有時是同行的學術爭鳴,有時是學生的課題研究,有些是研究生教育管理,有些是學校老師反映問題,有的甚至是陌生人的請求,他都會一一作答。
如果要說他最大的缺點是什么,熟悉他的人都會一致回答:不愿意說不。他給自己的生活塞滿了各種事情,自詡過的是“并聯生活”。每次見到他,他幾乎都在匆忙趕往下一站。即便是這樣,他從未敷衍過任何一個向他求助的學生、同事、朋友,甚至陌生人。他總能把每件事都做得有聲有色,“沒關系,我們一起來想辦法”,是他常說的一句話。在他這里,辦法總比問題多。
凌晨兩點。該睡覺了。
他推崇格拉德威爾的“一萬小時理論”,持續不斷的努力是從平凡到卓越的必要條件。他有太多事情要做,為了擠時間,十多年來始終保持著這樣的節奏。在上海時,他在復旦大學的辦公室總是凌晨一兩點鐘還亮著燈,除了出差,他在辦公室的時間表是周一至周日。他的鬧鐘固定地設在凌晨3點,不是用來叫早的,而是提醒他到點睡覺。這天凌晨四點要起床,準備出發去野外,他特意把“喊睡”鬧鐘提早了一小時。
窗外,月華如水,山的輪廓隱隱現現。
拉薩的夜,寧靜而美麗。
六、高山上的雪蓮
4點,起床。
粥已經煮好了,他拿出兩盤備好的小菜。學生們陸陸續續到他的宿舍集合,圍坐在一起吃早餐。“來吃早飯”,同學們已經習慣老師這樣的囑咐。
5點,出發。趕往墨脫進行野外科學考察。
墨脫,我國最后一個通公路的縣,是雅魯藏布江進入印度阿薩姆平原前流經的中國境內最后一個縣,也是西藏東南部最為偏遠的一個縣。在那一帶,有一片大約7萬平方公里的地區,50年來植物學家很少涉足。那里蘊藏著多少造物的滄桑與神奇。
一提起種子,鐘揚興奮得像個孩子。實際上,在藏地雪域采集種子的工作,枯燥而嚴謹:每種植物的樣本數量要達到5000粒,瀕危物種樣本一般需要500粒。為了保證植物遺傳信息獨立,每個樣本之間的距離不能少于50公里。早上五點鐘出發,晚上八九點鐘到達宿營點,一天奔波800公里已是極限。在宿營點還要連夜處理標本,夜里兩三點鐘才能睡下。
除了野外的科研工作,鐘揚還心系著墨脫的百姓。墨脫缺少經濟性作物,百姓生活還很貧困。2016年,鐘揚在墨脫種植了一片咖啡豆,他關心那些咖啡豆的生長狀況,想過去看看,“如果能種植出優質的咖啡豆,就能夠幫助當地百姓脫貧。”
幾年前,鐘揚曾去過當地最偏遠的背崩鄉上鈔希望小學。那是一位上海老人拿出自己的積蓄和離休金建起的學校。復旦大學學生連續多年在此利用寒暑假開展“圓夢墨脫”支教行動。這一次,他想再去那里看看,為160多名門巴族學生做科普講座,看看還能為他們做點什么。
他還在采集酸奶“種子”,去西藏的牧民家里,買牧民家自釀的酸奶,從中分離有經濟價值的優質菌種。他說,中國大陸生產的酸奶至今都是國外進口菌種,這意味著每喝一瓶酸奶都要給外國人交專利費。而西藏的酸奶是在空氣中完成發酵的,只有那里純凈的空氣才能做到。他要做出中國人自己的酸奶菌種。他的思考不僅僅停留在發表文章上,他想的是,能夠給這片土地和土地上勞作的人民帶來什么。
5月的青藏高原,山川相連,白云悠遠,杜鵑滿山。在鐘揚眼中,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奔波與尋找充滿樂趣。盡管常常要面對很長一段時間勞而無獲的沮喪,面對各種意想不到甚至是生死一瞬的狀況,回答團隊成員“那么累,為了什么”的困惑。
身旁,靜默的巖石、亙古榮枯的草木,都是生命長河跌宕起伏、周而復始的見證者。十多年扎根西藏,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在青藏高原做事,急不得,必須要做長期打算,一切都才剛剛開始。
他也曾迷茫過。曾經的他渴望成功,熱切地追求成功,青藏高原的生命百態讓他逐漸放棄“成功”。
他說,這個世界上只有極少數人在特定情況下能成為所謂的成功者。做些研究不是蠻好嘛,非要追求極致,一心想得大獎,往往就把事情做過頭了。
“這是一個關于失敗者與成功者的故事。”他在稿紙上寫下這樣一句話。2011年6月,他帶著學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高山雪蓮,學名鼠曲雪兔子。那是迄今為止中國植物學家采樣攀登到的最高點。尋找高山雪蓮的漫長過程,讓他對生命的意義有了更深的思考,他想把這些寫下來,拍一部《高山雪蓮》的電影,通過一個植物學家去西藏尋找雪蓮的故事,把登山和植物研究結合起來,向更多的人傳達一種精神。
在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巖石縫里,高僅10厘米、長著灰白小絨球花朵的鼠曲雪兔子,花形宛如拇指,是那么的不起眼。那是世界上分布最高的種子植物。僅從生物學特性看,和那些高大健壯的植物相比,它們大概算是典型的“失敗者”。但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干旱、狂風、貧瘠的土壤以及45℃的晝夜溫差。
鐘揚說,在一個適宜生物生存與發展的良好環境中,不乏各種各樣的成功者,它們造就了生命的輝煌。“更高、更快、更強”似乎是生命世界共同的追求。而生長于珠穆朗瑪峰的高山雪蓮,讓他看到了生命高度的另一種形式——
“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須迎接惡劣環境挑戰的時候,總是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的優勢,以換取整個群體乃至物種新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換言之,先鋒者為成功者奠定了基礎,它們在生命的高度上應該是一致的。”
這就是生命的哲學。
七、尾聲
未來和意外,不知道哪個先來。
2015年那場大病,他在病床上對友人說,一個人總要有走的那一天,不知道哪一天走。像我們這樣搞科學研究的人,生死來去都是想得非常透的。這些年,唯一愧對的是家人,特別是一對雙胞胎兒子,陪伴得太少。
一直奔忙在路上,家人擔心。他總是不以為然,嘿嘿一笑對妻子說:“我還有那么多事沒做完,老天爺不會把我收走的。”
誰也沒有想到,2017年9月25日,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讓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定格在53歲。那天,他就是在出差趕往機場的路上,清晨5點就出發了。
接到同事打來的電話,正準備出門去同濟大學上班的張曉艷在電話那頭喃喃地說:“他出這樣的事情,概率還是很高的。”
這些年,他一直在與時間賽跑。在他同事、學生、家人的回憶中勾勒出的2017年5月初的這兩個晝夜,只是他半生跋涉途中的一瞬。
在世界之巔無畏地奔跑,追逐夢想,就像夸父追趕太陽。他的心中始終有一個聲音在升騰——
腳踏實地,到人民中去,到廣闊大地中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這聲音來自遙遠的蒼穹,與他心中愿景的河流交匯壯大,讓他面對渺無人煙的空曠和對人類極限的無窮挑戰時,毫無畏懼。
20多年前,他就在入黨志愿書中立下自己的終身理想:“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祖國的科學事業發展貢獻力量!我會永遠堅定自己的信念,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
他是扎根大地的人民科學家。
他就像一棵大樹,因為根扎得深,他的生命之樹長出了一個個健碩粗壯的枝丫,努力向上,向著不同的方向,枝繁葉茂。
他就像一盞燈,點亮了無數人,溫暖是他生命的底色。
他就像一團火,赤誠熱烈是他生命最鮮亮的色彩。
天地能知許國心。
他留下了好多好多故事。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世界上寫故事。以無用之心求索,而得大用,以出世之心入世,而得大成。
他還有很多夢,在路上,在他身后,化出了一片桃林。
鐘揚曾說,生物學研究是一場持久戰。一百年后我肯定不在這個世界上了,但我的學生們還在,他們還會繼續走在我為他們開辟的道路上,早晚有一天,我們會發現那顆改變我們國家命運的種子。
一縷晨光照耀大地。山間,藏波羅花在沙石縫里盛開,風將蒲公英的種子吹散。風中,飄來他最愛的那首藏族民歌:
“世上多少玲瓏的花兒,
出沒于雕梁畫棟;
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
在高山礫石間綻放。”(記者 顏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