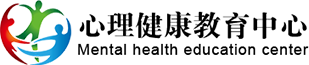同學們都覺得這題簡單......但我又沒聽懂,去問會被嘲笑吧......
ε=(′ο`*)))唉,
果然我就這個智商水平了,再努力也只能這樣......
——————
其實對于某些情況而言,以上類似心態的發生常常是因為某種畏難情緒而困擾。

“我不聰明,
成績也就這樣了。”
——真的嗎?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的一項研究對比了同卵雙胞胎(基因幾乎完全相似)與異卵雙胞胎(僅有部分基因相似)的突觸結構。
這項研究證明了許多研究的假設:
心智能力的高低取決于神經連接發展的強弱(新事物的刺激與反復練習),而非一出生就已決定。
成長心態:其核心信念是個體的能力和智力是可以通過努力和方法得當而發展的。
固定心態:也稱為固定型心態或固定思維模式,是指個體認為自己的能力和特質是固定不變的,不可改變的。

在一個早期的實驗中,德韋克和她的同事為紐約市七年級成績較低的學生講授有關大腦的知識以及有效學習的技巧。
半數人觀看了關于記憶的幻燈片,另半數人了解到:開發智力并不是讓智力自行發展,而是要通過努力和學習在大腦中形成新連接。完成課程后,孩子們回歸課堂,但教師不知道部分學生已了解刻苦學習能改變大腦。
在學年結束時,與秉持傳統觀點、認為智力水平在出生后就已定型的前一組“固定心態”的孩子相比,那些采納了被德韋克稱為“成長心態”、相信智力在很大程度上受自身控制的后一組學生,成了更主動的學習者,進步也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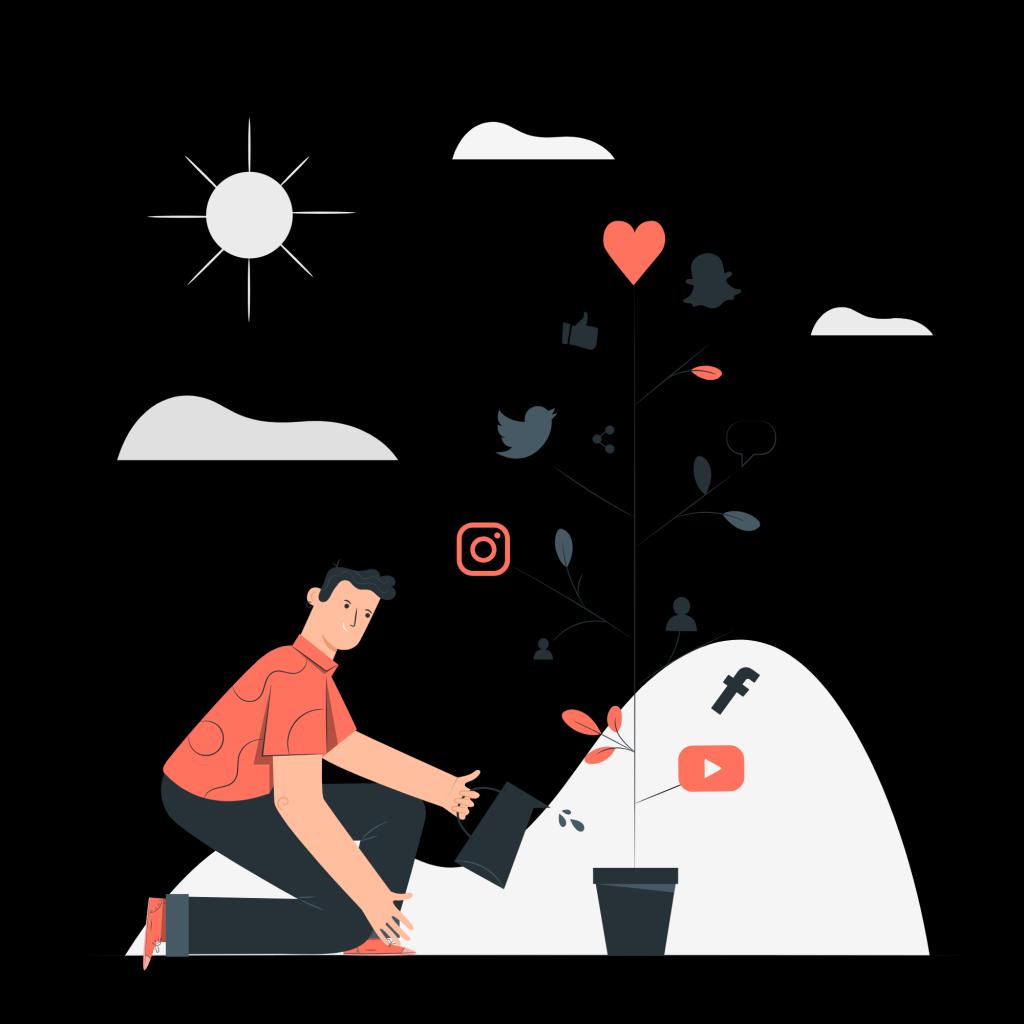
心理學家卡羅爾·德韋克的研究引發了諸多關注,因為她正好證明了只是信念,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學習與成績,也就是說,你要相信智力水平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自己手中。
“強調努力是在給予孩子一種他們能控制的變量,對于孩子來說,這樣的變量很稀有。”德韋克說,“強調天生的智力則是將它置于孩子的控制之外,對于應對失敗來說沒有好處。”
神經可塑性:大腦根據經驗改變和適應的能力,是指大腦改變、重組或生長神經網絡的能力。
學習與記憶均屬于神經處理過程,通過刻意訓練與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可以提高學習與記憶水平,這證明了神經可塑性的存在。

2011年,英國心理學與社會學團隊回顧神經學證據,發現大腦結構主要由基因決定,但神經網絡的精細構造也可由經驗塑造,并具有大幅修改的能力。
雖然基因在神經回路初期發展起重要作用,但人的神經回路并不像身體發育得那么早,而是一直持續變化至四五十歲甚至六十歲。
人在出生時大約有1 000億個神經細胞,它們通過突觸傳遞信號。正是這樣的回路,讓我們能夠感知、學習以及具備運動技能等。
有許多觀點認為人的智商在早期發育時已經被決定了上限,但是,神經學家帕特里夏·高德曼-拉奇克表示,雖然孩子早期大腦接收大量信息,但多數學習發生在突觸數量穩定后,從一年級到大學,突觸數量基本不變。學習主要發生在突觸形成較少的時候,然而,語言、數學和邏輯能力可以發展到成人水平。
哈里·T.丘加尼認為,大腦回路受經驗與環境刺激的影響可能主要在此時期,而非嬰兒期,這也使得每個人的神經結構不同。

用安·巴內特和理查德·巴內特的話來說,人的智力開發是“遺傳趨勢與生活經歷之間的對話,將會持續一生。”
軸突髓鞘形成一般從大腦后部開始,逐漸發展到前部,成年時發展到額葉。
額葉負責腦部功能的執行,處理高級推理、判斷和經驗技能。髓鞘厚度對應能力強弱,增加練習可強化相關領域的髓鞘,提高成績。
舉例來說,如果多練鋼琴,和手指運動以及音樂創作相關的認知過程對應的神經纖維髓鞘就會加速生成,而不從事音樂工作的人就不會出現這種變化。
艾利克森從研究中發現,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平均要在專業上投入一萬小時或十年的練習時間,而其中最為出色的人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獨自進行刻意練習上。
比如,莫扎特聽一遍曲子就能寫出樂譜。艾利克森認為,這種技能并非來自第六感,而是因為專業人士多年來在相關領域里積累了知識與技能,鍛煉出了超常的感知與記憶能力。
這里主要想說明的是,專家級的表現需要高質量的練習,而不是靠遺傳因素。

艾利克森、德韋克和他們的同事們在這一領域的工作告訴我們,自律、勇氣及成長心態這些素質才讓人敢想敢做,具備創造力與毅力,從而獲得更多的學問和更大的成功,而智商在這方面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我不聰明,成績也就這樣了。”誠然,條件不具足的情況下,有些成就水平不是我們一蹴而就的,但是不懷著“成長心態”去盡己所能地學習和訓練,我們又怎么確切知道自己能獲得多少進步?
總是“唯智商論”,然后因此故步自封,在某些情況下,并不利于我們的成長。智力水平并非天生已定,而且很大程度上由我們自己發展。我們所做的事情決定了我們發展怎樣的能力,做的越多,能做的也就越多。
如果容易焦慮,無須一開始就與已經有所成就者去對比,而是放下“畏難”情緒,為自己的每一分提升喜悅。
(撰稿/陳雪娜 編輯/陳雪娜 審核/禹敏 盧靈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