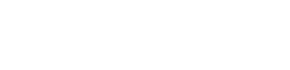2016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楊絳點煩本楊必譯< 名利場>》一書。該書在《編輯的話》中有這樣的說明:
楊絳先生關于文學翻譯的“點煩”論,曾在文學翻譯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引起眾多學者的贊譽和爭論。楊絳先生在其所撰的《翻譯的技巧》一文中稱:
簡掉可簡的字,就是唐代劉知幾《史通·外篇》所謂“點煩”。芟蕪去雜,可減掉大批“廢字”,把譯文洗練得明快流暢。這是一道很細致,也很艱巨的工序。一方面得設法把一句話提煉得簡潔而貼切;一方面得留神不刪掉不可省的字。
在這道工序里得注意兩件事:點煩的過程里不免又顛倒些短句,屬于原文上一句的部分和屬于原文下一句的部分,不能顛倒,也不能連接為一句,因為這樣容易走失原文的語氣;不能因為追求譯文的利索而忽略原文的風格,如果去掉的文字過多,讀來會覺得迫促,失去原文的從容和緩。如果可省的字保留過多,又會影響原文的明快。這都需要譯者掌握得宜。
翻譯理論家鄭延國先生撰文表達了對這段文字的理解。“不可或缺的工序;四是點煩的具體操作。顯而易見,點煩二字是學識淵博的楊絳從唐代史學家劉知幾那里借來的,顧名思義,便是‘簡掉可簡的字’,其目的是使譯文明快流暢、洗練凈潔,但卻是一道艱巨而細致的工序,運作起來必須格外‘留神’。首先,不能因為點煩而‘走失原文的語氣’;其次,不能因為點煩而‘忽略原文的風格’。換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處,正所謂:點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厭其多。”
筆者就此事訪問了鄭延國教授。鄭老師說自己的實際水平與那頂桂冠的距離太大了。只是平日里喜歡寫寫文章而已,其中一篇文章是《楊絳的點煩論》,公開發表了,不少網站也轉載了。想不到這篇文章居然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們派上了一點點用場。鄭老師希望青年教師在完成教學任務之余,抽出時間特別是利用寒暑假多寫些與專業有關的文章,藉此提高科研能力。(谷豐供稿)
引申閱讀:
楊絳的“翻譯點煩”論(中新網,2011年5月10日摘自香港《大公報》文/鄭延國)
http://www.chinanews.com/hb/2011/05-10/3030594.shtml
楊絳“點煩”本《名利場》出版:師生姊妹之作(澎湃訊,2016年11月12日)http://www.thepaper.cn/www/resource/jsp/newsDetail_forward_1559726_
楊絳姐妹“合譯”《名利場》出版(天津日報社城市快報,2016年11月15日)
http://epaper.tianjinwe.com/cskb/cskb/2016-11/15/content_7530346.htm
附件: